世纪轮回
尤瓦尔• 赫拉利近来一连出了两本畅销世界的书——《人类简史》与《未来简史》,我都跟风读了。尤其是我读《未来简史》,那感觉是《红楼梦》十二曲中的一句唱词——“忽喇喇似大厦倾”!一股暴发力,把我认为近乎公理的认知世界的模式给砸毁了。意识一片空无,茫然不知往后还“怎么做判断”、“怎么写”?

立即联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毕加索等一批丧魂落魄的巴黎画家。
法国发明家路易•达盖尔于1833年发明了照相机,到19世纪末,美国柯达公司接着发明了大众用照相机与胶卷,世界末日来临了,一批巴黎的写实主义画家,立即患上了集体恐惧症:完了完了!任何一位阿猫阿狗的画盲,只要拿着照相机咔嚓一下,就能绝对完胜我苦苦练了几十年的写实功夫(在二维平面上准确地画出人的三维视觉经验)!哦,我的上帝,那我以后还“怎么画”?说到上帝,德国哲学家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一千多年来,欧洲画家都在画《圣经》中上帝叙述的故事,即使主张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也都在画、在雕塑上帝的故事,仅仅是借此提升一下人而已。尼采这家伙证明上帝死了,那我们还“画什么”?
20世纪初惶惶不可终日的巴黎画家在黑夜里长吁短叹:怎么画?画什么?正因为这个惶恐,倒逼出了后来的“变形”(你照相机拍摄得极像,我们就来不像的)、“表现自我”(上帝死了,我就是上帝)的“现代主义”。
过了一百年的21世纪初,《未来简史》之于我,就像照相机之于写实主义画家。一个不祥的世纪轮回。尽管《未来简史》的书名有点文理不通(“史”者,过去所发生事的记述也;未来还没发生,哪来的“简史”?),可它,还是威逼我坠入被格式化了的万丈虚无!
又可敬又讨嫌的科学把神话和哲学都杀了
懵懂的童年。在天高云轻挂满星星的秋夜,母亲指着黄灿灿的圆月问,看见了吗?那是天仙嫦娥在月亮广寒宫里跳舞,那是吴刚在桂花树下酿酒,那是好多月兔在四处欢奔……从此,我不知有多少个明月夜,一个人痴痴地对着月亮寻找嫦娥、月兔。那感觉,很甜蜜还常会井喷出狂喜。甜蜜的是母亲的声音,狂喜喷发是因为我好像真在月亮朦胧的阴影里看到了嫦娥跳舞!
然而,然而等我上了学,可恨的科学,却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月亮是个死寂荒芜之球,诱发我天马行空想象力的那些抽象的月影与线条,不过是月球在多少亿年间被众多小行星撞出来的像麻子脸一样丑陋的环形山坑。
失落!沮丧!科学把多么曼妙神秘可享用一辈子不会衰减的神话给杀了!
科学还把爱智慧的哲学也杀了呢。
被誉为当代科学之神的霍金,在他的《大设计》一书的第一页就称:“哲学已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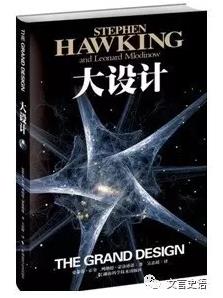
霍金在首页写道:“哲学已死。”
长大,我迷上了都说是最高智慧的哲学。苦读了很多书,虽似懂非懂,但更能刺激我总想彻底弄个明白而顽固地进取。好不容易分辨出了作为哲学根基的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等范畴,自认为就此获得了洞明世界的般若大智。哪知道,当我遭遇上了“薛定谔的猫”,得知了当今物理学中最前卫的量子力学证明,根本没有什么独立于精神之外的物质世界。譬如你看到了某个对象,那是你的意识导致了某个本来不确定位置的对象突然塌缩,然后其位置被确定,得到了你看到的样子。一阵龙卷风把智慧之树连根拔了:哲学家假想的物质与精神的世界二元态,原来是合二而一的互动共生体!
多少代哲学大智者建构出的像伟岸巨人的认识论,被量子力学拦腰一刀,倒地了!
“自由意志”也被生物学和脑科学给废了
《未来简史》发出讣告:当今天下奉为圭臬的神圣的“自由意志”死了!
什么是“自由意志”?“百度”称,自由意志是表达自由思维的意识选择做什么的决定,即意志的主动性。查查思想史,从苏格拉底,到斯宾诺莎,再到康德,历代哲人都在冥思苦想这个神奇神圣的自由意志。尽管定义不同,但都不容置疑地认定,人确实有自由意志存在。连犹太教、基督教也讲上帝创造的人有自由意志。夏娃有选择听上帝的教诲和听蛇的唆使的自由意志,人有选择上帝还是选择撒旦的自由意志,通过自由选择回归上帝。
赫拉利却冒千古与天下之大不韪,写道:自由意志是错觉,不足信。
从宏观来论,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原理就断然说了“不”。任何生物根本没有自由可言,哪来什么“自由意志”?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铁律,在掌控着所有生物(包括人在内)的生死簿。只有能无条件顺从环境的幸存者,将偶然所得的基因密码传给后代,方能不被灭绝而有繁衍下去的前景。其实生命很可怜,顺应变化不居的环境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宿命,其策略是多生,保证被环境和天敌杀害之后还有盈余。因此,生命界从来不会把每个个体生命看作神圣,“个人主义”在动物界是荒唐的痴人说梦。
从微观来求证,赫拉利说:“科学家(在人体上)没找到灵魂,没找到自由意志,只找到基因、激素、神经元,都遵守着与世界其他所有事物相同的物理化学法则。”
他引述了几个铁板钉钉子的科学实验。
1985年,神经科学家李伯特(Libet)做了一个弯曲手腕的实验。他交代受试者,在自己想弯曲手腕时用李伯特设计的精密时钟记下时间。另外,他在受试者头上戴了测试脑电图的头盔,观察大脑有关脑区的活动开启时间。石破天惊的实验结果出来了:受试者相关脑区开启活动的时间比受试者有意识决定弯曲手腕的时间要早550毫秒!见鬼,手腕弯曲是由大脑无意识感受发生的,有意识企图支配却在其后!大脑无意识首先做出了弯曲手腕的决定,有意识只是感受到了并执行这个决定,哪还有什么主观能动的“自由意志”存在?
1973年,斯坦福大学建造了一个逼真的监狱,让一群大学生志愿者扮演犯人与监狱管理员。监狱环境非常恶劣,让扮演管理员的受试者,想尽坏招从肉体到心理虐待犯人受试者。就这样延续一段时间后,无论犯人还是监管人员,都出现了不可控制的心理扭曲行为,真作假时假亦真,假戏真做起来,不得不立即停止实验。所谓理性的自由意志无影无踪,人们的行为完全由环境驱动。2001年,由Oliver Hirschbiegel执导,根据这个实验拍摄成了一部《斯坦福实验监狱》影片,震撼世界,获得德国电影三项年度金奖。
到了2011年,Haynes利用新发明的磁共振成像技术,再做李伯特按左右两个按钮的实验。其结果更是惊人,科学家提前10秒钟就从磁共振图像读到被试者会按哪个钮。这就是说,被试者脑的无意识的决定,比有意识决定提前了10秒!进一步证明所谓自主决定行为的自由意志就是幻觉。
那么大脑中无意识决定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呢?赫拉利称,是由“生物预设”(遇到外部刺激做出的反应)和随机事件触发的,这跟自由意志不相干。
因此,人类能用药物、大脑植入芯片、甚至毒品,随心所欲地驱动人产生相应的行为。实验同时证明,人与实验鼠的结果相同,从未发现有什么人所特具的“自由意志”冒出来顽抗一番而出现与老鼠不同的实验数据。近来美国军方还发明了一种“经颅直流电刺激器”头盔,只要戴上,就能让士兵去除所有杂念,专注于战场上某个特定任务。若让学子们戴上这种头盔,就能专注于设定的某门学科,使研究或考试赢得高分。如此这般,就成了原创发明者(即他者)的“设计意志”,泯灭了虚构的主体“自由意志”。

让大脑专注的“经颅直流电刺激器”
如果判定“自由意志”子虚乌有,那么,靠其作为理论主心骨的“自由主义”,还能挺直腰板去全球布道吗?曾把“自由主义”当作公理信奉的我,今后可怎么办?
“个人主义”价值岌岌可危
由“自由主义”衍生出来的、当下光芒四射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也十分不幸地遭到了现代科学的肢解。
“个人主义”,作为政治学概念,是由法国政治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首先创立的。在19世纪40年代,他在考察了美国9个多月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最先提出了"个人主义"这个概念,强调人是价值的主体,相信每个人都具有价值,因此高度重视个人的自我支配,自我控制,自我发展。美国学者萨姆瓦解释说,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包括自主动机、自主抉择、自力更生、尊重他人、个性自由、尊重隐私等层面。一言以蔽之:个人成了社会的终极价值;独立的个人,是社会的本源或基础。当下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把“个人主义”价值体系作为“核心价值”。
为什么“个人主义”(并非是中国扭曲诠释的“利己主义”)价值能如此高扬而被广泛接受呢?人们普遍相信它最符合人性,普遍猜想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个可靠的“自我”在实现个人自主的主义。自己的感受最真实真切。个人主导自己,能激发出强大的创造活力,体验到惬意多彩的人生。弗洛伊德还把“自我”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面,有人还附会地在大脑里找到了各自相应的位置。
于是,神经生理学家就从“自我”下手,设计实验,来求证是否存在真实可靠的“自我”。
科学家发现,人脑有左右脑两个部分各司其职:右脑处理空间信息,左脑处理语言和逻辑推理。据此他们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实验。让没有语言表述能力的右脑所掌管的左眼,看到一张色情图片,受试者立即开始脸红并咯咯笑了起来。研究人员狡黠地问笑什么?受试者做出回答的是掌管语言表述的左脑,它(右眼)并没有看到色情照片,因此不知道为什么笑,只好信口说了一句:“没什么。只是有光闪了一下。”这时主持实验者又让受试者的左眼(右脑)看了张色情图,受试者又笑了起来,还用手遮住了自己的嘴。研究人员追问:“既然是光闪了一下有什么好笑?”此刻管语言的左脑更是一头雾水,只好瞎编了一个可笑的原因,说,因为房间里有部机器看起来很好笑吧——这个实验证明,我们的“自我”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只要是左右眼接收的信息不对称,做出的语言判断根本就不可靠。人的左右脑会发生内战,一位二战老兵,成了脑裂患者,右手去开门,左手立即把门关上,永远开不了门!
接着,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也设计了一个实验。他请一组受试者参加一项分成三阶段的实验。第一阶段,让受试者把手放入14℃的冷水中60秒,冻得很难受,然后拿出来。第二阶段,将手放入同样是14℃的冷水中,同样感到刺骨难受,时间却增加到6分钟,只是在最后悄悄地向容器注入温水,使水温升到15℃。第三阶段实验是,研究人员对受试者说,你们可以自由选择认为比较不太难受的实验,或再重复做短时间实验,或重复做长时间实验。受试者的选择结果让人匪夷所思:有80%的人却选择了难受更长时间的长时间实验(第二阶段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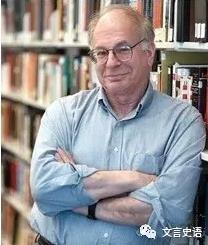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尔曼
这位卡尼曼,还与做肠镜的医生合作做了个相似的实验。根据病情,肠镜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插入观察的速度较快,疼痛的时间是8分钟。另一种是医生把动作放慢,疼痛程度与快插一样,时间却是快插检查的三倍——24分钟。两类被检查的受试者患者,每分钟都要报告痛的程度(以0~10选择表示,0是无痛,10是最痛)。最后的实验结果大悖常理:短时快插检查者的平均疼痛分为7.5,而痛苦时间增加3倍的长时检查者的平均疼痛分却只有4.5!个中原因是,慢检者因为时间长,最后会产生疼痛钝感,因此最后一分钟的疼痛报告是1,反而痛感值低了。
医生询问病人,假如要你重做一次,你将选择那种方式?绝大部分患者却对疼痛感要增加三倍的慢肠镜检查更青睐。何等滑稽可笑。
卡尔曼这两个实验证明什么呢?证明作为“个人主义”理论根基的“自我”,其表达出来的感觉,根本就与真实体验不符。那么,“自主动机、自主抉择”的“个人主义”的合理性乃至“合乎人情、顺乎天理”的神圣性就被颠覆了。
为什么“自我”会被误导?神经生理学家称,人的感觉在时间轴上,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体验自我”。冷、痛,时时由感觉系统体验到,但并不被记忆积累起来。还有一个自我是“叙述自我”,即把感受表达出来的自我,就会遵循“峰终定律”(Peak-end rule),即将体验的高峰值与终点值取平均数。那么,所谓“叙述自我”的叙述,就不可能是系列真实感觉之集合的真实描述。如果人依凭自己的“峰终定律”做决策,肯定是自欺而导致自害的愚蠢决定。一些政客就用上了峰终定律。第一任政绩平平,难以连任。但他在快到第一任结束时,加大惠民政策,让选民获得意外的收益,由峰终定律支配的民意立即飙升,连任取得成功。
我顺着这些实验生发开去,回顾人类历史,“个人主义”诉求,似乎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秉性。
数百万年石器时代的原始采集狩猎社会,人类就明白一个求生铁律:一个人会被猛兽吃掉,一群人会吃掉猛兽。《人类简史》称,7万年前,智人从非洲出来散布到世界各地,到农耕社会之前就灭绝了50%的50公斤以上的大型哺乳类动物(其中包括剑齿虎、猛犸象等猛兽)。那时的人绝对不会有个人自由独立的诉求,除非是疯子。
到了农耕社会,男耕女织家庭互补以及社会的家族式协作,才能求得温饱与繁衍后代。在中国,皇权与宗法权双管齐下管束所有人,此时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做好顺民孝子,别无他求,不然就会落荒而死。在西方,此时的个人都由全能的上帝管着,每个信徒虔诚信仰上帝,以及绝对顺从上帝在地上的代理者(教会)的管教,乃是天经地义。若有人追求个性自由、独到异见,伺候你的是火刑,还会告知你死后下地狱。农耕社会一万多年下来,没有任何考古证明,人类此时曾经大量显现过个人自由的诉求,更没有在受到皇权、教权严厉压制时整体人类的精神出现特殊病症的统计数据。
真正诉求把每个个体当回事,在西方要到5、6百年前文艺复兴人本主义兴起才起步。东方的仿效更晚更慢。
由此可见,“个人主义”虽然可能更符合当今人类的生存态,但并非符合天生的人性。
依据漫长的人类史,可以归纳出一条“个体与群体生存法则反比例定律”:个体生存越是依赖群体共生,其个性诉求就越弱;反之亦然。
请看生命界的蜜蜂、蚂蚁等高度群体化生存的昆虫,它们的个体诉求就为零。
赫拉利把自由主义者弄哑后果如何?
往昔,所有人文问题,可以争论几千年而莫衷一是。只需用一句“见仁见智”,就能圆通相容,双方再接着往下争,直至永远。因为,所谓人文学科的成就,不过是对某个问题的诠释,这次比以往更令人满意,如此而已。
然而,赫拉利不用形而上思辨,而是引证很多自然科学实验,由此导出结论。诸如自由意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真实自我等,在人脑认知系统中,不存在其建构起来的合理依据,不过都是虚构出来的一些概念。对付这样的重拳打击,反对者就不能用“见仁见智”的思辨再各说各话了,你必须也设计实验,除非能求得相反的数据,然后才能立论。历来被点赞的思想者那般舌战群儒的雄风,如今已是“东风无力百花残”了。
如果赫拉利之论真能成立,我忧心忡忡起来:那些极权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威权主义者,会不会变本加厉而且理直气壮地剥夺个人自由?
“让美国再次伟大”、“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还有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崇高号召,都在神圣化地应用“个体与群体生存法则的反比例定律”:群体目标设计得越伟大,个体对群体的依赖度将越大,那么个体诉求的价值就当越低。
倘若这样,人类的价值岂不又要再回没有个体诉求的石器时代-狩猎时期?情何以堪!
诚然,赫拉利在《未来简史》最后一章描绘了神话般的未来。他说人类将进入以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为母科学的数据主义,以取代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数据主义不会再争论“姓专制”还是“姓自由”,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谁的算法更优,谁能实现当时人类的永生、快乐、升级为神人,他就是最佳数据主义。可赫拉利再三声明,这不是预言,不是算命,只是一种可能性。
然而,那个像北极光一样华美的未来可能性,现在还是一个恍兮惚兮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而我当下怀着的大忧,有谁能解之?曹孟德的《短歌行》唱过:“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请问,哪里有新研发出的能解《未来简史》大忧的杜康酒呢?(封面图片来自网络,插图选自原作)
